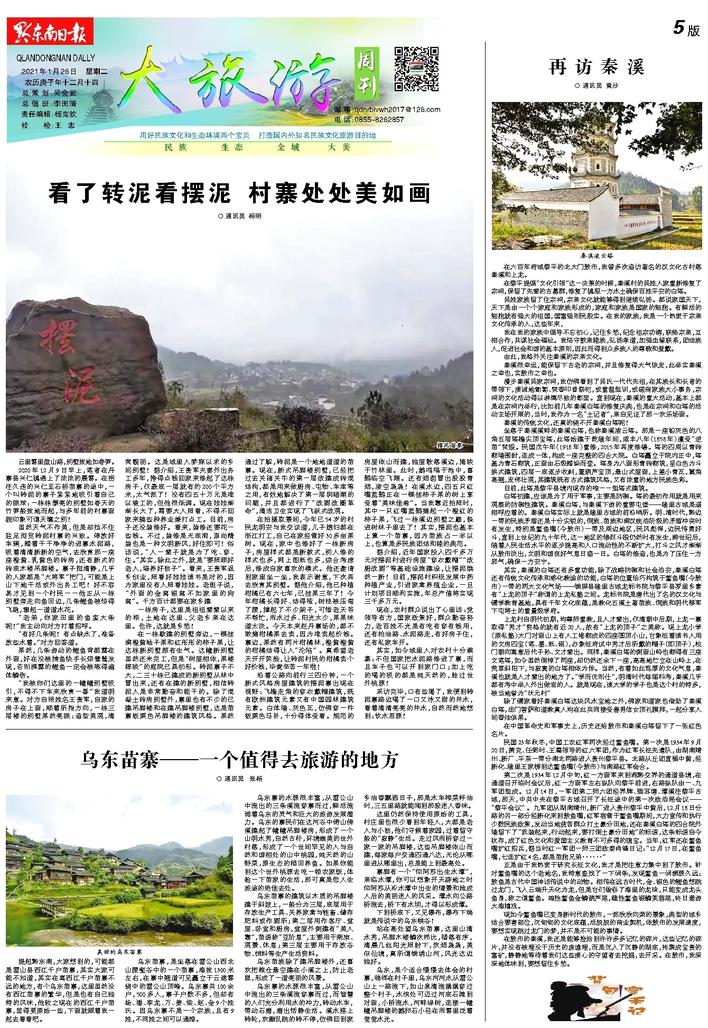○ 通讯员 黄沙
在六百年府城黎平的北大门敖市,我曾多次造访著名的汉文化古村落秦溪和上龙。
在黎平提倡“文化引领”这一决策的时候,秦溪村的吴姓人家重新修复了宗祠,保留了先辈的古墓群,修复了镇服一方水土确保百姓平安的白塔。
吴姓家族留了住宗祠,宗亲文化就能够得到继续弘扬。都说家国天下,天下是由一个个家庭和家族形成的,家庭和家族是国家的细胞。有鲜活的细胞就有强大的祖国,国富强则民殷实。在我的家族,我是一个热衷于宗亲文化传承的人,这些年来,
我在我的家族中倡导不忘初心,记住乡愁,纪念祖宗功德,联络宗亲,互相合作,共谋社会福祉。我恪守敦亲睦族,弘扬孝道,加强血缘联系,团结族人,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原则,因此而得到众多族人的尊敬和爱戴。
由此,我格外关注秦溪的宗亲文化。
秦溪很幸运,能保留下古老的宗祠,并且修复得大气恢宏,此举实秦溪之幸也,实敖市之幸也。
漫步秦溪吴家宗祠,我仿佛看到了吴氏一代代先祖,在其族长和长者的带领下,虔诚地匍匐、焚香叩首祭祀,或重温组训,或磋商家族大小事务,宗祠的文化活动得以淋漓尽致的彰显。直到现在,秦溪的重大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宗祠内举行,比如前几年秦溪白塔的修复庆典,也是在宗祠和白塔的活动主场开展的,当时,我作为一名“土记者”,亲自见证了那一欢乐场面。
秦溪的传统文化,还真的绕不开秦溪白塔呢!
坐落于秦溪溪畔的秦溪白塔,也称秦溪凌云塔。那是一座铅灰色的八角五层塔檐尖顶宝塔,此塔始建于乾隆年间,咸丰八年(1858年)遭受“逆苗”焚毁。民国戊午年(1918年)重修,2015年再度修缮。塔的四周以青砖砌墙围封,连成一体,构成一座完整的四合大院。白塔矗立于院内正中,塔基为青石砌筑,正面由石级踏垛而登。塔身为八面形青砖砌筑,呈白色为斗拱式建筑,四层一底逐步收刹,置葫芦宝顶,悬山式屋面,上盖小青瓦,翼角高翘,宏伟壮观,其建筑既有古式建筑风格,又有浓重的地方民族色彩。
目前,此塔是黎平县境内现存的唯一一组塔式建筑。
白塔初建,应该是为了用于军事,主要是防御。塔的最初作用就是用来观察的防御性建筑。秦溪白塔,与秦溪下游的重要屯堡——隆里古城是遥相呼应着的。秦溪白塔实际上就是隆里古城的前沿哨所。明、清时代,黔边一带的民族矛盾还是十分尖锐的,侗族、苗族和满汉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鳌鱼嘴(今敖市)一带及周边地区,民风彪悍,边民恃勇好斗,直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这一地区的惨烈斗殴仍然时有发生,跨世纪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人口流动性的不断扩大,打斗之风才渐渐从敖市淡出,文明和谐良好气息日盛一日。白塔的修造,也是为了压住一方邪气,确保一方安宁。
其实,秦溪的白塔还有多重功能,除了战略防御和社会治安,秦溪白塔还有传统文化传承和感化教谕的功能,白塔的位置恰巧构筑于鳌鱼嘴(今敖市)一带的两大文化气场——锦屏县隆里古城龙标书院与黎平县罗里乡素有“上龙的顶子”称谓的上龙私塾之间。龙标书院是唐代出了名的汉文化与儒学教育基地,具有千年文化底蕴,是教化五溪土著苗族、侗族和明代移军下屯将士的重量级学府。
上龙村自明代初期,均尊师重教,且人才辈出,仅清朝中后期,上龙一寨取得“秀才”资格的就有近20人,故有“上龙的顶子”之美称。现上龙小学(原私塾)大门对面山上有人工堆砌成的四座圆顶小山,它象征着读书人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亦象征府试中秀才后所戴的帽子(即顶子),校门朝向寓意后代子孙、文才辈出。同样,秦溪白塔的侧面山岭也砌得有三座文笔塔,如今虽然倒掉了两座,却仍然还余下一座,高高地伫立在山岭上,在荒草斜阳下,与寂寞的白塔相依为伴。当然,有着如此笃厚的文化气息,秦溪也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了。“学而优则仕”,明清时代每届科考,秦溪几乎都有考中举人外出做官的人。就是现在,读大学的学子也是这个村的特多,被当地誉为“状元村”
除了儒家看好秦溪白塔这块风水宝地之外,佛家和道家也借助了秦溪白塔,法门菩萨和道教真人均在此共同接受善男信女顶礼膜拜,一起分享人间香烛供果。
在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上,历史还给敖市和秦溪白塔留下了一张红色名片。
民国23年秋冬,中国工农红军两次经过鳌鱼嘴。第一次是1934年9月20日,萧克、任弼时、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由湖南靖州、新厂、平茶一带分南北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北路从丘团直插中黄,经新化、隆里王家榜到达鳌鱼嘴(今敖市)与南路红军会合。
第二次是1934年12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来到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境,在通道召开临时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左右纵队向黎平前进,右路纵队由一、九军团组成。12月14日,一军团第二师六团经界牌、猫耳塘、潭溪往黎平古城,那天,中共中央在黎平古城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 。九军团从湖南靖州,新厂进入贵州黎平中黄后,12月18日分路的另一部分经新化来到敖鱼嘴,红军宿营于鳌鱼嘴期间,大力宣传和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发动当地贫苦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还在秦溪白塔的四合院外墙留下了“武装起来,行动起来,要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这条标语自今犹存,成了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瑰宝。当年,红军还在鳌鱼嘴扩红招兵,据当时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委肖锋日记:“12月17日,在鳌鱼嘴,七连扩红4名,都是苗胞兄弟······”
正是由于我热衷于研究长征文化,我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敖市。针对鳌鱼嘴的这个老地名,我特意查找了一下词条,发现鳌鱼一词溯源久远:敖鱼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动物。相传在远古时代,金、银色的鲤鱼想跳过龙门,飞入云端升天化为龙,但是它们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只能变成龙头鱼身,称之谓鳌鱼。雄性鳌鱼金鳞葫芦尾,雌性鳌鱼银鳞芙蓉尾,终日遨游大海嬉戏。
现如今鳌鱼嘴已变身新时代的敖市,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典型的城乡结合要害部位,沉甸甸的文化底蕴,活脱脱的商业契机,依敖市的发展速度,要想实现跳过龙门的梦,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敖市的秦溪,我还是能够捡拾到许许多多记忆的碎片,这些记忆的碎片,并没有被埋没于历史的废墟理,而是沉入了沉静的湖底,抟聚成宝贵的富矿,静静地等待着我们这些虔心的守望者去挖掘,去开采。在敖市,我深深地体味到,要想留住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