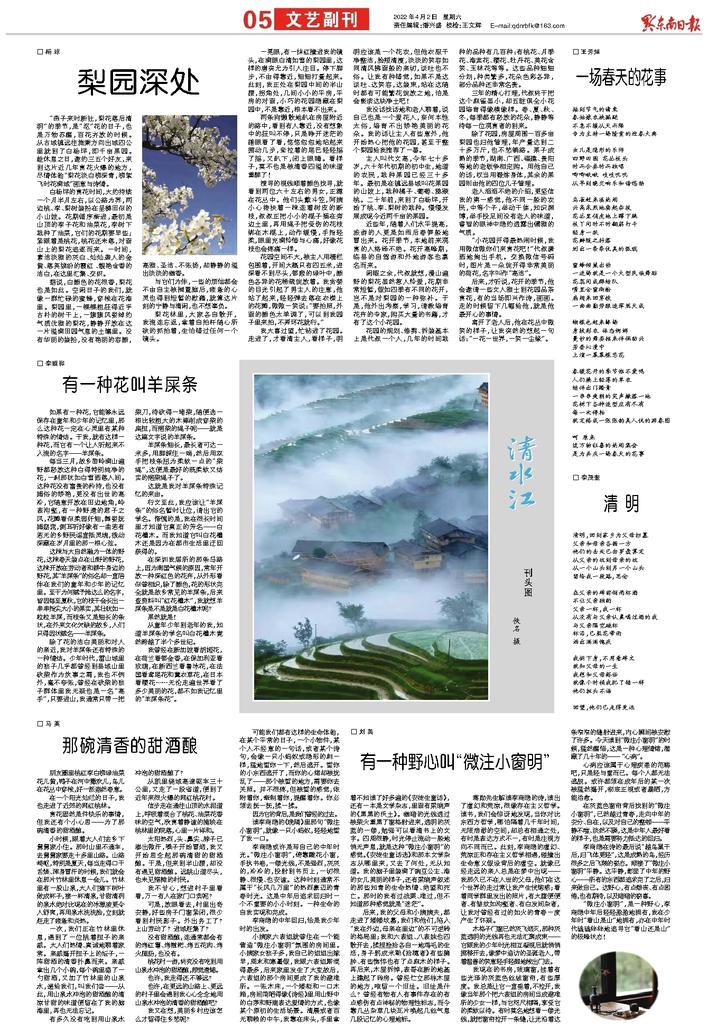□ 李顺骅
如果有一种花,它能够永远保存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那么这种花一定在心灵里有某种特殊的情结。于我,就有这样一种花,而它有一个让人听起来不入流的名字——羊屎条。
每当三月,故乡苗岭满山遍野都怒放这种白得特别纯净的花,一刹那犹如白雪洒落人间。这种花没有富贵的矜持,也没有媚俗的娇艳,更没有出世的高冷,它随意开放在田边地角,岭表沟壑,有一种野遗的君子之风,花瓣看似柔弱纤细,舞姿妩媚窈窕,侧耳听好像有一曲若有若无的乡野民谣直抵灵魂,拨动深藏在岁月里的那一根心弦。
这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野花,这株春天装点在山野的野花,这株开放在劳动者和耕牛身边的野花,其“羊屎条”的俗名却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至于为何赋予她这么的名字,皆因每至夏秋,它的枝干会长出一串串指尖大小的果实,其壮犹如一粒粒羊屎,而枝条又是细长的条状,在外来文化欠缺的故乡,人们只得因状赋名——羊屎条。
除了花的洁白美丽和对人的亲近,我对羊屎条还有特殊的一种情结。少年时代,雷山城里的孩子几乎都曾经到县城山里砍柴作为炊事之需,我也不例外,毫不夸张,曾经在砍柴的孩子群体里我无疑也是一名“高手”,只要进山,我通常只带一把柴刀,待砍得一堆柴,随便选一根比较粗大的木棒削成穿柴的扁担,而捆柴的绳子呢——就是这篇文字说的羊屎条。
羊屎条细长,最长者可达一米多,用脚踩住一端,然后用双手把枝条扭为柔软一点的“柴绳”,这便是最好的既柔软又结实的捆柴绳子了。
这就是我对羊屎条特殊记忆的来由。
行文至此,我应该让“羊屎条”的俗名暂时让位,请出它的学名。惭愧的是,我在很长时间里才知道它真正的芳名——白花檵木。而我知道它叫白花檵木还是因为在都市生活里迂回获得的。
在深圳我居所的那条马路上,因为南国气候的原因,常年开放一种深红色的花卉,从外形看似曾相识,除了颜色,花的形状完全就是故乡常见的羊屎条,后来查资料叫“红花檵木”,我就想羊屎条是不是就是白花檵木呢?
果然就是!
从童年少年到老年的我,知道羊屎条的学名叫白花檵木竟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我曾经在新加坡看胡姬花,在荷兰看郁金香,在保加利亚看玫瑰,在新西兰看鲁冰花,在法国看鸢尾花和薰衣草花,在日本看樱花……无论走遍世界看了多少美丽的花,都不如我记忆里的“羊屎条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