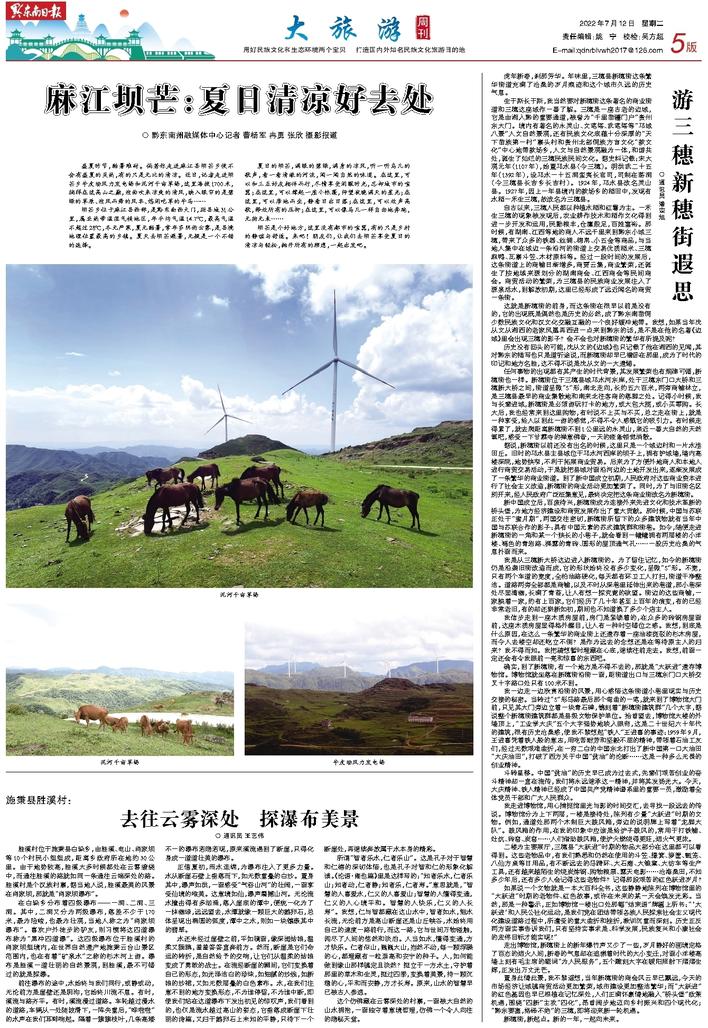○ 通讯员 潘宗旭
虎年新春,刹那芳华。年味里,三穗县新穗街这条繁华街道充满了沧桑的岁月痕迹和这个城市久远的历史气息。
生于斯长于斯,我当然要对新穗街这条著名的商业街道和三穗这座城作一番了解。三穗是一座古老的边城,它是由湘入黔的重要通道,被誉为“千里苗疆门户”贵州东大门。境内有著名的永灵山、文笔塔、武笔塔等“邛城八景”人文自然景观,还有民族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天下苗族第一村”寨头村和贵州北部侗族方言文化“款文化”中心地带款场乡,人文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和谐共处,诞生了灿烂的三穗民族民间文化。据史料记载:宋大观元年(1107年),始置邛水县(今三穗)。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设邛水一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司制在荡洞(今三穗县长吉乡长吉村)。1924年,邛水县改名灵山县。1927年,因上一年县境内的款场乡的稻田中,发现有水稻一禾生三穗,故改名为三穗县。
自古以来,三穗人民都以种植水稻和红薯为主。一禾生三穗的现象被发现后,农业耕作技术和稻作文化得到进一步开发和运用,民勤粮丰,仓廪殷足,百姓富裕。那时候,有湖南、江西等地的商人不远千里来到黔东小城三穗,带来了众多的铁器、丝绸、棉帛、小五金等商品,与当地人集中在城边一条沿河的街道上交易优质稻米、三穗麻鸭、瓦寨斗笠、木材原料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这条街道上的商铺日渐增多,商贾云集,商业繁荣,还诞生了按地域来源划分的湖南商会、江西商会等民间商会。商贸活动的繁荣,为三穗县的民族商业发展注入了源泉活水,到解放初期,这里已经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一条街。
这就是新穗街的前身,而这条街在很早以前是没有的,它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成了黔东南苗侗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交融互融的一个良好缓冲地带。我想,如果当年沈从文从湘西的老家凤凰再西进一点来到黔东的话,是不是在他的名著《边城》里会出现三穗的影子?会不会也对新穗街的繁华有所提及呢?
历史没有回头的可能,沈从文的《边城》也只记载了他在湘西的见闻,其对黔东的描写也只是道听途说,而新穗街却早已横卧在那里,成为了时代的印记和地方名胜,这不得不说是沈从文的一大遗憾。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其发展繁荣也有规律可循,新穗街也一样。新穗街位于三穗县城邛水河东岸,处于三穗东门口大桥和三穗新大桥之间,街道呈微“S”形,南北走向,长约五六百米,两旁商铺林立,是三穗县最早的商业集散地和南来北往客商的落脚之处。记得小时候,我与长辈进城,新穗街是必须游玩打卡的地方,或大包大揽,或小买零购。长大后,我也经常来到这里购物,有时说不上买与不买,总之走在街上,就是一种享受,给人以到此一游的感觉,不得不令人感慨它的吸引力。有时候走得累了,就去爬距离新穗街不到1公里远的永灵山,亲近一番大自然的天然氧吧,感受一下甘霖寺的禅意佛音,一天的疲惫顿觉消散。
据说,新穗街以前还没有出名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城边村和一片水洼田丘。旧时的邛水县主县城位于邛水河西岸的坝子上,拥有护城墙,墙内高楼深院,地势狭窄,不利于拓展商业贸易。后来为了方便外地商人和本地人进行商贸交易活动,于是就把县城对面沿河边的土地开发出来,逐渐发展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这些商业资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新穗街的商业活动更加繁荣了。同时,为了与旧街名区别开来,经人民政府广泛征集意见,最终决定把这条商业街改名为新穗街。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新穗街成为连接外来先进文化和技术革新的桥头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商贸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时候,中国与苏联正处于“蜜月期”,两国交往密切,新穗街所留下的众多建筑物就有当年中国与苏联合作的影子:具有中国元素的苏式建筑群和街巷。如今,随便走进新穗街的一角和某一个狭长的小巷子,就会看到一幢幢拥有两层楼的小洋楼、褐色的青岩路、裸露的青砖、圆形的屋顶通气孔……一股历史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是从三穗新大桥这边进入新穗街的。为了留住记忆,如今的新穗街仍是沿袭旧街改造而成,它的形状始终没有多少变化,呈微“S”形。不宽,只有两个车道的宽度,全柏油路硬化,每天都有环卫工人打扫,街道干净整洁。道路两旁全部都是商铺,以及不时从深巷里延伸出来的巷道,那小巷深处尽显清幽,长满了青苔,让人有想一探究竟的欲望。街边的这些商铺,一家挨着一家,约有上百家,它们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演变,有的已经非常老旧,有的却还崭新如初,期间也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店主人。
我信步走到一座木质房屋前,房门是紧锁着的,在众多的砖钢房屋面前,这座木质房屋显得格外醒目,让人有一种时空错位之感。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这么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还遗存着一座油漆斑驳的杉木房屋,而今人去楼空却还屹立不倒?是作为远去的念想还是在等待原主人的归来?我不得而知。我把猜想暂时埋藏在心底,继续往前走去。我想,前面一定还会有令我眼前一亮和惊喜的东西吧。
确实,到了新穗街,有一个地方是不得不去的,那就是“大跃进”遗存博物馆。博物馆就坐落在新穗街沿街一面,距街道出口与三穗东门口大桥交叉十字路口处只有100米不到。
我一边走一边欣赏沿街的风景,用心感悟这条街道小巷里现实与历史交接的秘密。当转过“S”形马路最后那个弯曲的一笔,就来到了博物馆大门前,只见其大门旁边立着一块青石碑,镌刻着“新穗街建筑群”几个大字,据说整个新穗街建筑群都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抬首望去,博物馆大楼的外墙顶上,“工业学大庆”五个大字强势地映入眼帘,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建筑,很有历史沧桑感,使我不禁想起“铁人”王进喜的事迹:1959年9月,王进喜凭着铁人般的意志,用吃苦耐劳和坚毅不屈的精神,带领着石油工友们,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东北打出了新中国第一口大油田“大庆油田”,打破了西方关于中国“贫油”的论断……这是一种多么无畏的创业精神。
斗转星移。中国“贫油”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式,先辈们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却一直在流传,我们将永远继承这一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今天,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里的重要一员,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
我走进博物馆,用心捕捉馆里光与影的时间交汇,去寻找一段远去的传说。博物馆分为上下两层,一楼是接待处,陈列有少量“大跃进”时期的文物。例如,通道处那两个木制巨大鼓风箱,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龙脚大队”。鼓风箱的作用,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给炉子鼓风的,常用于打铁铺、灶炕、砖窑、炭窑……人们借助鼓风箱,使炉火燃烧得更旺,烟火气更浓。
二楼为主要展厅,三穗县“大跃进”时期的物品大部分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这些老物品中,有我们熟悉和仍然在使用的斗笠、撮箕、箩筐、甑笼、八仙方桌等日用品,有不断远去的马蹄环、大石磨、大锥窠、大纺车等生产工具,还有越来越陌生的烧炭炼钢、购物粮票、露天电影……沧海桑田,不知多少年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些老物件?记得那段艰苦的红色跃进岁月?
如果说一个文物就是一本大百科全书,这些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大跃进”时期的老物件、红色故事,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焕发光彩。当然,那是一种警示,正如博物馆一楼出口处那幅“结束语”牌匾上所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中,所遭受的重大曲折和挫折,教训沉重而深刻。历史正反两方面实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发展,民族复兴和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
走出博物馆,新穗街上的新年爆竹声又少了一些,岁月静好的画境定格了百态的烟火人间,新春的气息却在追溯着时代的大小变迁,对面小洋楼高墙上刻有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五个雕刻大字在暖阳照射下熠熠生辉,正发出万丈光芒。
置身此情此景,我不禁遥想,当年新穗街的商会风云早已飘远,今天的市场经济让城镇商贸活动更加繁荣,城市建设更加整洁繁华;而“大跃进”的红色基因也早已根植在记忆深处,人们正满怀豪情地融入“桥头堡”政策机遇,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昂首阔步地迈向乡村振兴和四个现代化;“黔东要塞,络绎不绝”的三穗,即将迎来新一轮机遇。
新穗街,新起点。新的一年,一起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