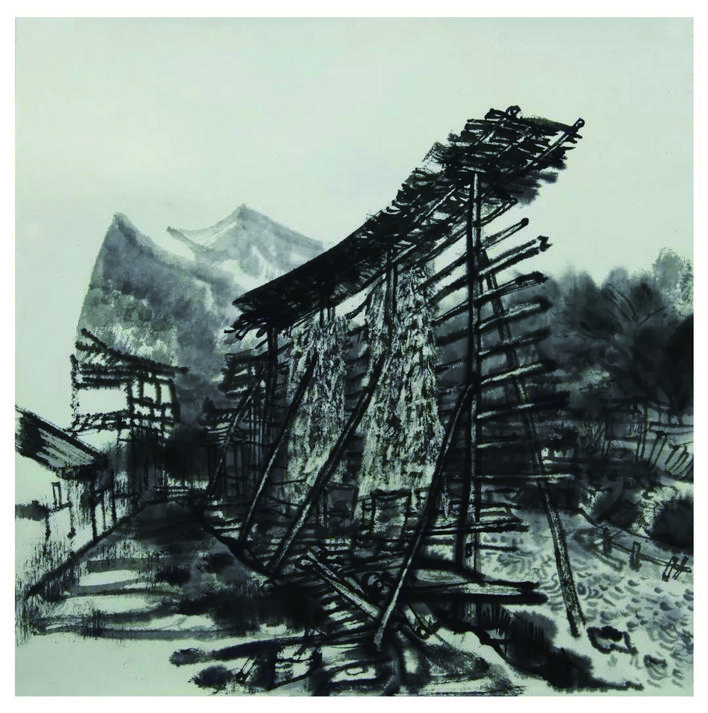□ 马昌辉
与务林相识,其实是一场不经意的邂逅。
为探访一块曾镌刻过一段历史公案的石碑,在吃过午饭后,我和师弟伍文剑便驱车向从江县西山镇岑杠村走去。盛夏时节,刚经历过两场暴雨,一出县城,便到处塌方,车子沿着泥泞的被淹得只剩半边的公路小心翼翼前行。本是半个钟头的车程,我们整整走了一个钟头才来到岑杠村。找到石碑,经过一番清洗、辨认、拍照,并了解一些情况后,已是下午四点过钟。此时,伍师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邀请他去参加老家党支部提前举行的“七一”建党节活动。于是,我们继续向一个叫捞里的寨子前行。
这里已远离县城三四十公里,处在县城的东南面,是山地向丘陵的过渡带,坡度已相当缓和,由于这里更处东南方向,气候更为温润,草木长得更为茂密,植被极为良好,所以不再看到道路塌方,只是不断看见有汩汩流水从溪沟里流出,才想到之前下过暴雨。车子沿着水泥公路弯弯绕绕了一阵子,便来到了捞里村。将车停靠在村口的停车场后,我们朝村里看去,却看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伍师弟于是掏出电话打过去,才知道活动地点原来不是在这里,是在村委会所在的另一个自然寨“老寨”。
走了不到五分钟,来到老寨。此时,活动都已基本结束。党员们分散在村委楼前闲聊。我们来到办公室,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员们及村干连忙热情打招呼、让座、倒茶。本次活动只剩下的最后一项活动即是聚餐,吃“交心饭”。
离开时,伍师弟说,要去看老房子一眼。伍师弟的老房子在务林寨,于是,我们便驱车再盘过山去。
抵达务林时,已是黄昏。薄暮横空,不肯散去的余晖从明亮的天边投来,给长空上掠过的薄云虚拟出一抹淡淡的橘红。夕空下,郁郁苍苍的山,起伏环绕。务林,一个坐落于半山腰的寨子,就这样,岁月静好地隐现于天地草木间。寨上的木屋,鳞次栉比,碧瓦飞甍,即将没入苍茫的暮色中。屋外,守望相助的路灯,开始发出诱人的光芒。
苍茫的暮色下,映衬出后山的轮廓和黛色的古树林。寨子的前边,是一块比较宽阔的菜地,菜地大约有十亩见方,呈椭圆形,原来应该是一座小山包。寨子倚山而建,面向菜地,两侧山岭自山顶下延成环抱状,把寨子和菜地都环抱其中。在寨子和菜地的中间有一段坳颈,已被夷平硬化,刚打造成供人们休闲的场所。篮球场上,有许多孩子在玩,女的追逐,男的嬉闹。
伍师弟家就在休闲场地的最里边,我们从右边的一栋木屋绕过去。来到屋子的后边,伍师弟说,你等下,我先进里面去开灯。灯亮时,我才看到,刚才从外边看到的砖砌一楼,在里边变成了栅栏木墙。木墙的主要架构是杉树枝和横木方,简单修理的三根木方上中下横陈,只脱去外皮的杉树枝,两根一组,每隔二三十公分穿过木方交互夹着,在树枝的空隙间,宛如填空题般填进去的,只是用斧头破开来的粗糙木板。木墙上,还煞有介事地挂着有了些许年岁风尘的草帽、镰篓。打开房门,来到里面,紧靠木墙的地方,还有一套老旧的碓子,碓脚还是石头打造成的。伍师弟的这些安排布置,让我一下子寻回了那些逝去的久远时光。“到外边来坐!”当伍师弟指出外边已装扮一新的外间说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说:“哦,不,不了。”
伍师弟早已搬到县城,父亲前几年也不在了,几个哥哥另有住宅,且常年在外打工,房子已经没人住了,只是有个在家的侄儿帮着看管。我没问伍师弟怎么不把它拆了,但我想,房子存在的价值,或许就是过年时,来与父老乡亲相聚,来感受一下那份温馨的亲情,来温习一下那份纯澈美好的初心。
在务林,我们没有逗留太久,前前后后不过半个钟头。离开时,天已全黑。在路过一处空地时,伍师弟说,这块地是自己的,曾经想开发来做生意。我想了想,说:“搞鱼塘养鱼吧!”伍师弟表示赞同。
我们都到了知天命之年,早就知道了该何去何从。“这世间,终将是尘归尘,土归土,有什么再值得去汲汲营营。把山还给山,把水还给水,把心灵、把生命、把一切的一切都还给自然。”这是务林这块纯净山水给我的生命启示。